文化神经症:对人的重现发现
霍妮脱离传统精神分析的重要标志就是她对神经症的定义,她认为:
“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做神经症。”
在这一界定中,霍妮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精神分析的内在心理机制;另一方面又为神经症的界定置入“文化”的前提,即“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
基于此,霍妮正式将文化这一议题置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使得神经症成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同时,霍妮并未止步于对神经症的外延进行界定,而是深入探讨了神经症的文化性内涵。

卡伦·霍妮(1885.9.16-1952.12.4) 医学博士、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在霍妮早期的思想中,她倾向于将“文化”同“神经症”划等号,即个体的心理困扰根源于社会文化环境,而非生物性本能。
至于文化为何如此关键,霍妮认为“首先,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
就霍妮所讨论的恐惧而言,实际上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原发性的恐惧,即个体降生于世后所体验到的无助与不安,被她称为“基本焦虑”。基本焦虑存在于所有文化中,无法被消除,构成了个体最初的动力。二是继发性的恐惧,即“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固有的典型困境,这些困境作为种种内心冲突,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日积月累,就可能导致神经症形成”。
在这一层面,文化所引发的个体压抑与内在冲突是未分化的,即文化就是压抑与冲突本身,个体无非是这种压抑与冲突发生的场所,映照着这种压抑和冲突的镜子。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霍妮细致考察了美国的“竞争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她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权力、名望和财富必须通过个人自己的努力去获得,那么个人就不得不进入与他人的竞争。这种竞争以经济为中心,辐射到所有一切活动之中,并渗透到爱情、社会关系和游戏之中。
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竞争无疑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无怪乎我们发现它在神经症病人内心的冲突中始终占据着一个核心的地位”。与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相对,基督教教义则强调奉献与友爱,宣扬“爱邻如爱己”的主张。基于此,个体的单一行为无法同时实现社会文化倡导的两种对立的价值,个体也就不断体验着文化中的对立与冲突。
霍妮还将文化的重要意义延伸到了家庭互动之中。同传统精神分析学派一样,霍妮也强调早期亲子互动对个体一生的决定性影响。具有颠覆意义的是,霍妮看到了父母角色的真正内涵,即文化的载体。这就意味着亲子互动并非个体间的行为,而是父母代表着社会文化与子女互动,从而将促使子女内化一定的社会文化。
基于这种逻辑,“文化人”或“社会人”才正式取代“生物人”,成为神经症层面的第一主体。这样“文化-父母-子女”的桥梁就正式被搭建起来,人不仅仅是文化中的人,更是文化本身。
霍妮在其早期工作中将文化置于首要位置,虽是对弗洛伊德的超越,却又维持了决定论的思想,化“本能决定论”为“文化决定论”。这一论断实质上将个体的困扰怪罪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心理冲突的复杂性。霍妮在精神分析中重新发现了人,却又将人符号化、简单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霍妮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逐渐回归到主体内在的探讨。
自我结构:对人本身的回归
霍妮在其晚期的著作《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中正式提出了她的自我结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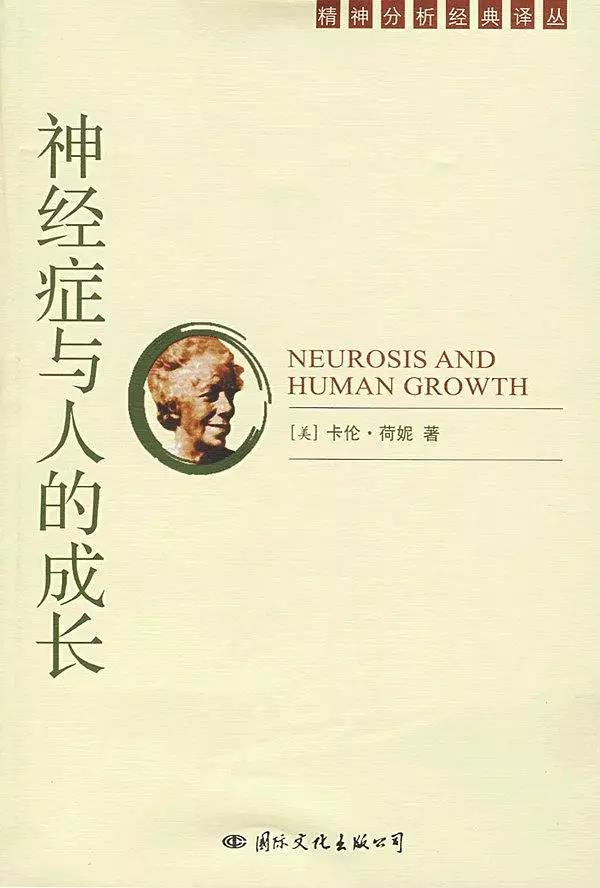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霍妮将神经症个体的“自我”(self)划分为三个部分:
真我(real self),即个体所具有的潜能,代表其不受神经症束缚的情况下所能自我实现的程度;
理想自我(idealized self),即个体受其神经症人格驱动所希望成为的幻想式的自我,也被称为“不可能自我”;
实我(actual self),即个体在现实中所体验到的自我。
这一结构实为对文化神经症理论的修正与整合。一方面,精神分析对文化的考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霍妮在临床实践中又重新意识到了个体内在动力的重要意义。在她看来,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神经症个体与正常个体是质的转变而非量的差异,对这一“质变”的考察不能仅仅立足于文化环境,而必须回归到人格本身。
与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我-自我-超我”纵向人格结构相比,霍妮的自我结构是“水平的”、“表层的”,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再创造,并通过创造实现了回归。
霍妮对真我的描述是含混不清的,真我作为自我潜能的根源,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只可体验却难以言说。真我的提出是霍妮对传统精神分析最大的“背叛”,相对于传统精神分析悲剧性的人性观,霍妮通过真我赋予了人根本性的向上的活力。
在她看来,正是由于真我的存在,精神分析治疗才有存在的价值。通过治疗,个体最终能够重新体验到真我的力量,基于此,精神分析治疗不应助人“前进”,而只需助人“回归”其本然状态。这实为对人性的积极肯定,也是对霍妮自己提出的文化决定论的扬弃,体现了她的人本主义倾向。
正是通过对真我的观察,霍妮明确认识到了个体的内在本质是先于文化的,虽然文化对人的压抑是必然的,但却无法决定人。
霍妮对理想自我的论述则阐明了文化在个体层面的运作。在她看来,理想自我是在后天由文化塑造的,而这种塑造的具体手段则是亲子互动。父母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与子女进行互动的过程中,将一定的社会价值与观念传递给子女。这些观念逐渐内化为个体意识或潜意识中的“应该”(should),即个体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何人。个体看似做出了选择,但这种选择却是被文化要求的一种被迫选择,其选择的对象也只是一种虚幻,根本无法实现。
由于神经症个体无法意识到这种“应该”的虚假性,其行为多表现为强迫性,即“我必须这么做”,霍妮称这种现象为“应该之暴政”。理想自我则通过这种暴政压制真我,阻碍自我的潜力的实现。在这一逻辑链条中,文化以理想自我的形式侵入,最终触及了个体的真我部分,实现了对人的异化。
结合霍妮对真我的阐述,她认为理想自我所代表的文化虽然至关重要,但却不应对神经症负全部责任。她回顾对“竞争文化”的讨论,表示“产生于竞争文化中的对追求成功的 ‘强迫性驱力’ 事实上并无法为人们的神经症辩护,因为即使在竞争的环境下,对很多人而言,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有关乎人的成长的价值观——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来得重要”。
对同一议题的观点的转变,霍妮回归到了对人自身力量的探讨,将人的真正价值归还给了主体。
实我则直接表现为在真我与理想自我的双重影响下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个体每时每刻都在意识层面体验着的。在霍妮看来,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通过对言说着的实我的倾听,找到真我与理想自我的话语,并帮助个体理解这些话语。个体通过对自身的理解,最终能够实现对真我的“回归”。
因此,在霍妮这里,实我是作为达到真我的桥梁而具有重要意义,实我是精神分析治疗的可能性的基础。
*本文为李卓轩老师原创文章,版权为作者本人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与我们联系。原创不易,转载请与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