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技术出发,照例要首先考量这种受虐狂极端且明确的病理形式。我已在其他地方[3]描述过,分析治疗中,我们是如何发现这类病人的,鉴于他们针对分析治疗效果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将之归因于一种“无意识的”负罪感。我曾提出过一个用以识别这类人的迹象(一种“负面治疗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而且并未隐瞒下述事实,即这种冲动的强度构成了最强的阻抗之一,也是实现我们医疗或教育目标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无意识负罪感的满足或许是主体从疾病所获(通常是复合的)利益最有力的堡垒——同康复作斗争、拒绝放弃患病状态之集大成者。神经症正是因其所带来的痛苦而对受虐倾向具有价值。很有启发意义的是,我们发现,与所有的理论和预期相反,如果主体陷入一桩痛苦且不幸的婚姻,或失去所有钱财,又或者患上严重的器质性疾病,之前使种种治疗工作无法生效的神经症反倒消失了。这种情况下,一种形式的痛苦被另一种形式的痛苦取代了;并且我们发现,关键的是,可能总得维持一部分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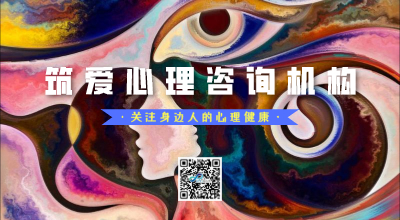
当我们向病人说起无意识的负罪感,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他们很清楚,最折磨人的东西表现了出来——问心有愧——一种有意识的负罪感,一种的负罪感的察觉,而他们也因此不愿承认自己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保有与之类似的冲动。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弃用“无意识负罪感”这一心理层面不正确的术语,而代之以恰如其分涵盖我们的观察的“对惩罚的需求”(need for punishment)一词,便可满足他们的反对意见。但我们切不可像对有意识负罪感那样,让自己在评判和定位无意识负罪感时有所克制。
我们已将良知的功能归于超我,也认识到意识的负罪感是自我和超我之间张力的一种表现。感到未能满足其理想,即超我,所提出的要求时,自我会反应出焦虑感(有意识的焦虑)。我们想知道的是,超我如何扮演这个苛刻角色,以及与自身理想不同时,自我为何会感到害怕。
我们已经说过,自我的功能是统一与调和它所服务的三个机构的要求;我们可以补充一点,这样做的同时,它也在超我中拥有一个可以努力遵循的模式。因为这个超我既是外部世界的代表,也是它我的代表。超我由它我力比多冲动最初的客体——即双亲——内摄而成。这个过程中,与这些客体的关系被去性化,偏离了其直接的性目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克服俄狄浦斯情结。超我保留了被内摄者的关键特质——他们的力量、整肃,以及监视和惩罚的倾向。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过的[4],很容易设想,多亏本能在内摄进自我的过程中分离了出去,超我的严整度才得以提升。超我——在自我中起作用的良知——对它所负责的自我可能会变得严酷、残忍,而又挥之不去。因此,康德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直接继承人。
但是,尽管这些不再作为它我的力比多客体的角色继续在超我中起到良知的作用——它们仍属于现实的外部世界。它们从外部世界而来;其的力量背后隐藏着往昔和传统的所有影响,这正是现实(reality)最强烈的表现之一。由于这种相辅相成,超我,俄狄浦斯情结的替代物,成了现实外部世界的代表,也从而成为了自我竭力参照的榜样。
如此一来,俄狄浦斯情结被证明是——正如历史意义上已经推测的[5]——个体的伦理感与道德的来源。儿童发展过程导致了与父母的日渐疏离,而他们在个人层面对超我的重要性也退居幕后。他们所留下意象(imagos)一度与教师和自选的榜样、公认的英雄之类的权威联系在一起,而自我已经变得更具抵抗力,不再需要内摄这些角色了。这一系列源于双亲角色中的最后一种,是命运的黑暗力量,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将它视为非个人化的。没有人会反对荷兰作家穆尔塔图里(Multatuli)[6]把希腊人的Μοία (命运)换成‘Λόγος χαί’ Αυάγχη‚(理性与必然性)这个神圣的对子;但只要把对世界的引领权让渡于天意、上帝,或上帝与自然,就会带来这样一种迷信,即在神话学意义上把这类终极的、最遥远的力量看作双亲,并相信自己与他们通过力比多纽带连接在一起。在《自我与它我》中,我也试着从类似的双亲命运观中引申出人类对死亡的现实恐惧。似乎一个人很难从其中解脱出来。
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回到对道德受虐狂的考量上来了。我们已经提到,从他们在治疗和生活中的行为来看,尽管他们对这种极端道德没有丝毫的意识,然而这类个体给人的印象仍是,受到过度的道德抑制,处于极度敏感的良知的支配之下。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种道德的无意识延展和道德受虐狂有什么不同。前者强调的是自我所服从的超我的高度施虐狂;后者强调的是自我本身的受虐狂,不论是向超我还是向外部的父母力量,它都寻求着惩罚。我们一开始混淆这两者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自我和超我(或与之等同的力量)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两种情况下涉及的都是一种通过惩罚和痛苦来满足的需要。那么下面这个细节绝非无关紧要:超我的施虐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意识,而自我的受虐倾向仍是一种对主体隐藏起来的规则,必须从他的行为中才能推断出来。
道德受虐狂是无意识的,这一事实将我们引向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我们可以将“无意识负罪感”这一表达解释为从双亲权力手中求取惩罚。我们现在知道,经常在幻想中出现的被父亲殴打的愿望与另一种愿望——与父亲有一种被动的(女性的)性关系——很接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种退行性变形。如果我们将这一解释纳入道德受虐狂的内容,其隐含意义就清晰了起来。良知与道德是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克服和去性化产生的;但通过道德受虐狂,道德再次性化,俄狄浦斯情结复苏,道德向俄狄浦斯情结退行的道路打开了。这既不利于道德,也不利于当事人。诚然,一个人可能与其受虐狂一道保留了全部或某种程度的伦理感;但另一方面,其良知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消失在其受虐狂中。另外,受虐狂会诱发种种“有罪的”行为,它们得靠施虐狂良心(sadistic conscience)的谴责(正如许多俄罗斯人性格类型所证明的那样),或者靠命运那强大的双亲力量的惩罚来赎罪。为了激起命运这一双亲代表的惩罚,受虐狂必须做不合时宜的事,必须违背其自身利益,必须毁掉现实世界中向其敞开的前景,或许还必须摧毁其自身的现实存在。
当对文化对本能的压抑阻碍了主体的大部分破坏本能在生活中得以运用,受虐狂就会规律性地掉转向自身。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后撤的破坏性本能在自我中表现为受虐狂的加剧。而良知这一现象,使我们推测,从外部世界折返的破坏性也被不经任何转变地吸纳进了超我,并增强了对自我的施虐。超我的施虐狂和自我的受虐狂相辅相成,并联手产生了同样的效果。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本能的压抑如何能——经常或相当普遍地——导致一种负罪感,才能理解如何一个人越克制对他人的侵犯,其良知就越发的严厉而敏感。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受厌倦攻击行为的文化浸染,那么他就会因此而敦厚良善,且不会对自我多加怀疑。似乎伦理要求(ethical requirements)是首要的,并且从中产生了本能摒弃。而这样并未解释伦理感的起源。事实上,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最初的本能摒弃是由外部力量强制实现的,并且正是外部力量创造了伦理感,而伦理感在良知中得以表露,并要求着进一步对本能的摒弃。
因此,道德受虐狂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经典例证。其危险在于这一事实,道德受虐狂起源于死本能,并对应于这种本能中未能外化为破坏本能的部分。但另一方面,既然它具有色情组分的意味,那么,没有力比多的满足的话,主体也就不会自毁。
[1]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g)。
[2]见《幼儿期生殖结构》(The Infantile GenitalOrganization, 1923e)。
[3]《自我与它我》(The Ego and the Id, 1923b)
[4]《自我与它我》
[5]见《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1912-13)第四章。
[6] E. D.Dekker (1820-87)